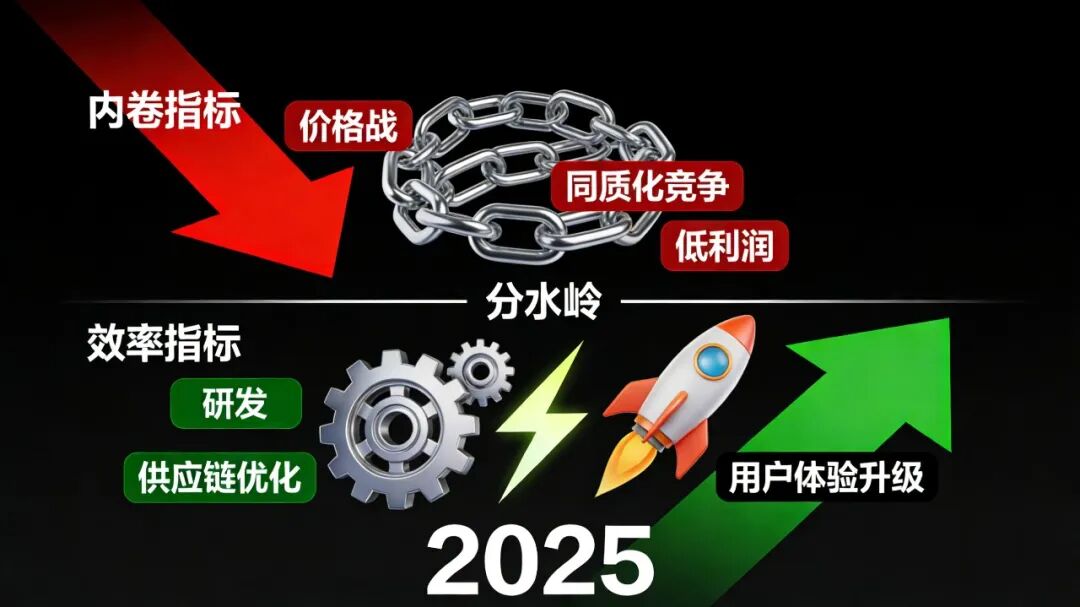去年7月,全球首款L3自动驾驶量产车奥迪A8正式发布。该在60km/h以下的低速条件下,能够实现拥堵路况中的自动驾驶,而驾驶员完全可以从方向盘上解放双手,把注意力转移到其它方面而不需要继续观察路况。
这引来了一些主机厂的趋之若鹜。尤其在国产品牌中,无论是奇瑞、长安、长城还是造车新势力里的小鹏等还将实现L3自动驾驶量产作为了企业"四化"目标之一,并且给出了明确时间表。
但几乎是同期,另一家主机厂沃尔沃也进行了公开表态,明确表示要放弃L3。无独有偶,福特在自动驾驶方面路径的选择也是直接越过 L3,从 L2 实现 L4 全自动驾驶。
按照福特的逻辑,L2 是特定的辅助驾驶技术,可以帮助驾驶员更好地驾驶,主要的责任人是驾驶员。L4则是全自动驾驶汽车,汽车接管所有控制权,驾驶员不用承担责任。
而作为夹在其中的L3 ,它的挑战在于未能给车辆和驾驶员划分一个清晰的责任认定:到底是人还是机器在驾驶。
因此,也有人认为L3是法律的噩梦。
L3到底是鸡肋还是熊掌?2018年,7月26日,由高德地图举办的2018未来交通峰会在京举行。在"驶"向未来-汽车新生态论坛的讨论环节中,来自知名 Teri1、OEM以及法律界人士对于自动驾驶L3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持人是《汽车商业评论》总编辑、汽场联合创始人贾可。
自动驾驶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贾可(《汽车商业评论》总编辑、汽场联合创始人):一个问题,近两年大家都在很兴奋的谈论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这个事。对于无人驾驶来讲,一种说法是觉得它太美好了,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一种说法是觉得它是乌托邦,虽然很好,但是要达到是很难的。
所以,对于大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王忻(安波福亚太地区工程总监):我刚才在我的演讲中提到再安全也不安全,我的困惑是自动驾驶一直是要探索很多没有预测的领域。所以,对我来说困惑是几件事情。一是如何落地,因为现在很多的技术还都是飘的比较多,落地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让老百姓用得起自动驾驶车,虽然从0开始,我们有123的分级,我自己的车最多是L0,什么时候大家都能用上L2,什么时候大家都能用上固态激光雷达给我们带来的好处,这也是我工作当中一直在探寻怎么能够把它尽快商业化,把它的价格拉下来的目标实现,150块钱固态的激光雷达能够落地。
另外,自动驾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如何给老百姓带来对他们真正有用的功能。比如说在碎片时间、堵车的时候,能不能先把这个自动驾驶利用起来,如果这个自动驾驶能利用起来,对老百姓来说自动驾驶才能实实在在的做下去。
王忻:我们最主要的困惑是两件事情。第一,怎么能够把它做得更安全,把刚才所说的冗余、设计全部放进去,安全、再安全一点。每次出去做测试,总是能发现一些问题,到最后做测试的结果永远会发现有一些问题一直要去解决。
第二,很多问题用固态激光雷达可以有效的规避掉,但是基于现在的成本价格,我们又很难去实现。所以,只能通过软件的冗余算法尽可能的解决掉,但是还不能完完全全解决掉。

李戈杨(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副总裁):从千寻的角度来讲,自动驾驶是我们未来规划几个大规模高精度场景最重要的一个场景。自动驾驶与理想主义不太一样,它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事一定会实现。
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的服务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包括政策法规它的适应性。千寻只做了其中一个细分的技术,就是我们把高精度变成了一种公共服务。除了高精度要变成公共服务之外,其他的道路基础设施其实都要做大规模的改造,才能够适应未来自动驾驶时代真正的到来。
每个企业的发展都有自己的难点,每个阶段的难点都不太一样。现阶段,我们在技术上更多的关注是其他新兴技术对绝对定位的影响。千寻非常关注的是跟5G的融合,跟卫星技术的融合,这也是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布局的重点。
第二,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多定位手段的融合。这也是我们在迎接自动驾驶时代到来关注的一个重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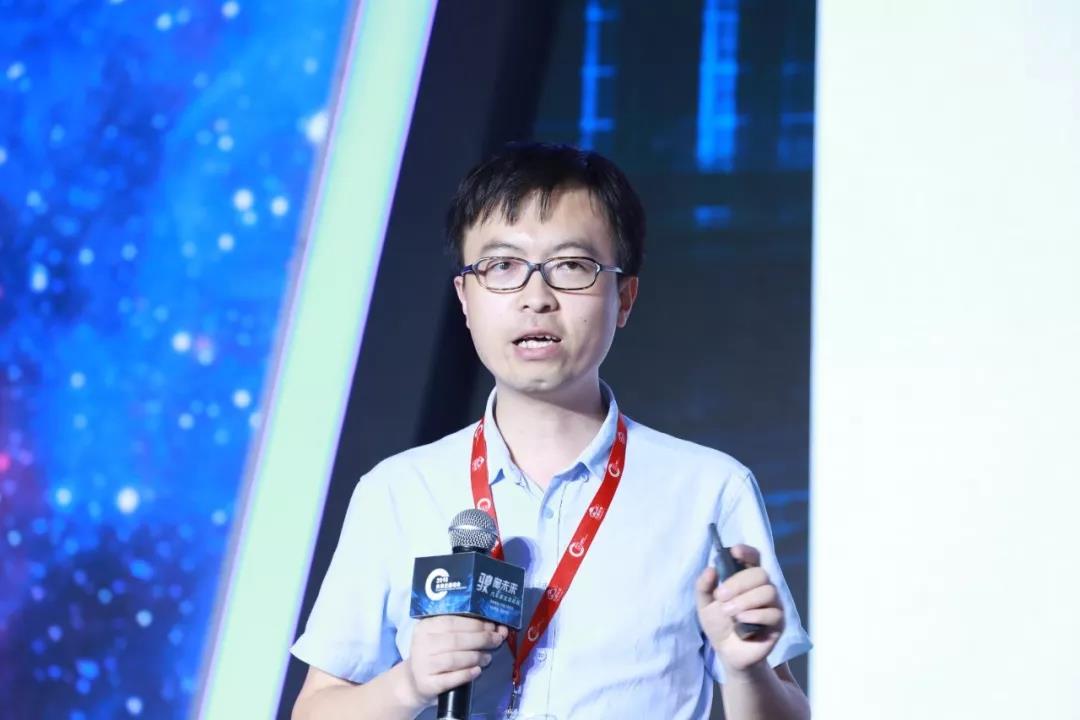
薛俊亮(恒润智能驾驶事业部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困惑太多了,比如大家都没有实现L5,这是最大的困惑。
另外有几个困惑,一个是我们应该从12345往上走,还是有些人提的我们从54321往下降。这是一个可能的困惑,我也在想答案。比如说Google自动驾驶公司,说他们是直接干到第五级慢慢往下降,也有的是12345这样走的。
我觉得没有谁对谁错,客观规律如此,大家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只不过Google或者我们的很多公司,他们走了横向控制、纵向控制,逐渐的越走越好,走到比较高级以后,再从高级打磨,再逐渐往下走,这是一种路子。
另外一种路子是一步一步往上走,每一步都变成了产品,逐渐做到最高级的产品。这可能是一种解释,换句话说,没有人是空中楼阁,每个人都有了12345,只不过大家是不是把一级、二级变成了拿得出手的产品,还揣在兜里再直接往上加,最后憋出一个大招。
比如说我们做TGA我们做低速,我们的困惑是低速好做,还是高速好做。奥迪A8做L3还是在60公里/时以下,CT6可以在高速公路上放开走。刚才法律专家讲了高速公路上建议更多的是去做测试,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发现高速公路上相对简单一点,因为高速公路上车少,尤其是在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低速的时候可能会有行人,可能会有自行车,甚至有牛、有大象跑来跑去。还有一些人喜欢低速的时候挤来挤去。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做低速的自动驾驶我感觉也是很难的,所以到底低速好做,还是高速好做,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困惑。
第三个困惑留给法律专家给我们解读,CT6可以放开手,这件事情到底合法不合法。

赵雷(车和家战略副总裁):说到自动驾驶从分级来讲。我比较困惑的是L3的分级,我们会从用户体验的角度去思考。我们自己孵化的公司做到2.5,会将第一辆量产车推给消费者。
人是要参与到驾驶中的,只能暂时的松开,还要保持对驾驶状态的关注,这是L2.5。L4是可以不关注了,它分的很清楚,可以关注,也可以不关注。但是L3不太清楚,什么情况下介入,什么情况下不介入,很难去区分。所以我们把2.5做得很好,让大家感受非常好,我们的战略目标是L4,L5我觉得很遥远,这是一个包括社会问题在内的很全面的问题,是短期内很难达到的。所以,我们整个公司的战略是瞄L4。
自动驾驶在立法上的难点
贾可:去年我去过华盛顿,参加过关于自动驾驶的立法听证会,有卡车司机在那儿强烈反对,说他们会失业。先说一个我的困惑,一般新兴产业政策上的突破,包括新能源汽车,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够迅速的突破,因为政府的权力很大,立法上比国外容易得多。中国立法上还有什么不能突破的?何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何姗姗(智联出行研究院自动驾驶汽车法律中心主任):先讲一下我的困惑。真的是出于对自动驾驶的热爱,我们很早就开始研究各国相应的立法,到现在位置最困惑的一点是技术在不断创新,而且我们国家的商业模式在不断创新。像网约车、互联网金融,这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但制度创新在这个阶段特别重要,它要为技术做到很好的引导和监督的保驾护航的作用。我们现在主要在做制度上的创新,怎么解决技术上和商业模式之间衔接的问题。
您提到的这个问题,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其实测试阶段和商用化阶段是不一样的。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测试阶段安全员应该时刻关注周边驾驶环境以及谨慎驾驶的义务还在你身上,没有丝毫的改变。在公开道路上测试,在我们国家的要求是应该扶着方向盘,这是法规的要求,当然你可以不去操控方向盘。
Uber的那个案子,后来美国交通部的调查结果是当时安全员根本没有在关注驾驶,所以才导致了此外严重的事故。所以,测试阶段不存在L3、L4、L5的问题,因为安全员就是一个普通的驾驶员的角色,只不过你不操控,但是精神的紧张程度和关注程度丝毫不亚于传统的驾驶员。未来商用化阶段,L3、L4、L5确实是完全不同的责任划分模式。
尤其是刚才您讲的L3级别,法律的恶梦原来我们都是套用在L3层面上,到底人和系统怎么去划分。其实德国已经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尝试,他的模式是我先单刀直入解决2、3的问题,车内要安装监控系统,如果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要提醒他。即使有一些时刻是可以手不扶方向盘,但是你的意识还是要在驾驶这件事情上。因为德国的立法还是把驾驶员即使在L3级别功能启动的情况下,驾驶义务也丝毫没有改变,还是要时刻保持清醒,这比传统开一辆车要求还要高。日本也采用这个思路,通过法律法规告诉所有的消费者,你的驾驶义务丝毫没有改变。这是一种思路。
另外一种思路,比如美国现在的立法没有采用这个思路,在他的立法当中有一个板块叫消费者教育。规则体系不是直接把这么难的问题都扔给驾驶员,而是商家要对消费者进行充分的教育,使其了解这个功能到底是怎么用的。传统的是考了驾照之后,车的说明书你看吗?你可能从来不看,但在传统的法律上,如果说明书上有黑体字,特大号字,那就叫充分提示你注意。如果说明书里充分提示了你应该注意驾驶,但是你也不会看这个说明书,这就说明你重视的不够,所以美国立法补充的进去。其实我们国家想做,速度会推进的很快,关键的问题是各部委的协调,尤其是交通、公安、工信部,有管车的生产的,有管道路安全的,有管交通设施的,现在都融合在一起之后,比如道路交通设施上装了一个通信的信号,到底归谁管?因为通信标准是归工信部管的。所以,有没有可能从国务院的角度有更高的领导关注这件事情。
去年7月份国务院关于人工智能的规划,实施的效果很好,很快各部门就去协调,做测试规范了。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感受来讲,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