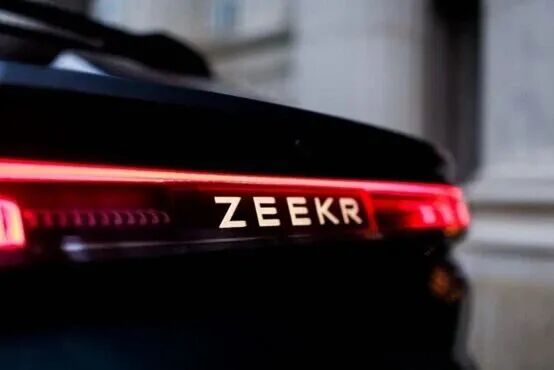无人驾驶是百年汽车工业的一个崭新高度,也是人们对智慧出行梦寐以求的目标。
今年以来,从拉斯维加斯电子商品展上各种无人驾驶技术的高调亮相,到许多汽车和科技公司陆续对无人驾驶商业计划的激进宣示,一些媒体开始大肆宣称无人驾驶会比人们想象的时间更早到来。
当前社会上和业界弥漫着一种浮躁,似乎无人驾驶就在眼前,谁不抓住它就会被淘汰,造成了资本市场的压力和业界的普遍焦虑。
无人驾驶真的指日可待了吗?
我的回答非常简单:否。不仅否,还非常遥远。
主观能动性是无人驾驶的必要条件
要问为什么,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无人驾驶和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位于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的顶端。按照美国自动车工程学会(SAE)对自动驾驶的五级分类,第一级至第三级为有人的自动驾驶,或称为辅助自动驾驶,即人仍然要为驾驶的最后决策负责。在这些阶段,所有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只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驾驶体验,尤其是安全体验。
第四级和第五级为无人自动驾驶,即可以将人完全排除在驾驶决策之外,其中第四级为有限场景、第五级为无限场景下的无人驾驶。显然,第四级和第五级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
本文所探讨的无人驾驶是指以人类出行为目的的第四级和第五级汽车自动驾驶。
第四级无人驾驶可以在某些特定的场景下较快地实现,但它不会对汽车工业产生颠覆性的改变,这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去买一辆只能在规定道路上或规定区域内行驶的无人驾驶汽车。

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正如美国交通部部长赵小兰女士年初在底特律车展上所说:我们热爱汽车,因为我们热爱自由。限制自由的无人驾驶汽车可能只是公共交通的延伸,不会取代今天面向个人拥有汽车的巨大市场。
要实现无限场景下的无人驾驶,安全即是初衷,也是最大的障碍。我们必须明白汽车是一件非常独特的产品——它量大面广并涉及人们必要的日常出行,而更重要的是它与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发展无人驾驶技术的首要目的是提高其安全性。
由于汽车驾驶过程中每个场景都不会重复而且复杂多变,在高速行驶中稍有差错就有付出生命代价的可能,所以要求无人驾驶必须具备类似人类合格驾驶员那样能够凭主观意识举一反三的主观能动性——这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主观能动性,而是指无人驾驶在遇到任何不熟悉或突发场景时都能够主动地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操作,而且可以比人做得更好,从而取得高于人类驾驶的安全性。
在我们目前所处的交通环境中,一辆没有主观能动性的无人驾驶汽车无疑是巨大的安全隐患,有违无人驾驶安全第一的原则。
为了降低甚至替代无人驾驶对主观能动性的依赖,人们想象了一种理想化的情景:厘米级别的高精地图覆盖所有汽车可以到达的地方;道路上的每一辆汽车都具备车对车、车对系统的智能互联以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而且还具备行人与车分离的客观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无人驾驶汽车即使不完全具备主观能动性,也能在预定的道路上安全地自动驾驶,犹如今天智能制造工厂中广泛应用的全自动运输机(AGV)一样。
目前某些接近这种条件的应用场景正在出现,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第四级别有限场景下的无人驾驶。但是,要使所有场景满足这些条件显然是一项涉及整个社会生存空间变革浩瀚而巨大的工程,绝非一家或几家企业甚至一个产业能够完成,在可见的未来几乎不会成为现实。
因此,主观能动性是无人驾驶的必要条件。没有主观能动性的无人驾驶,是对科学的不尊重,是对生命的轻视,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
主观能动性条件尚未成熟
如何才能实现主观能动下的无人驾驶?路径可能有很多,但目前广为采用并寄予厚望的是人工智能技术。
什么是人工智能?简单地说,就是用人造的机器(比如计算机)来实现人的感知和决策功能。人工智能技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早期的语言文字处理到今天的图像语音识别,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近年来,基于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为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如医疗、家居、娱乐、制造、服务等。

然而,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处于初始的阶段,还不具备支撑无人驾驶所需要的主观能动性的能力。
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将人的智能分为三个层次:1)感性;2)理性:3)灵性。
感性即通过类似条件反射那样获得的信息和知识,如被电炉烫了一次就不会再去触摸电炉。
理性即通过人的逻辑思维得出的知识,如做出如果电源关闭就可以清洗电炉这样的逻辑判断。
而灵性则是人在一定的感性和理性思维基础之上的智慧思维,包括人的自我认知、意识、情感以及主观能动性。例如人可以安全地利用电炉创造出各种美味佳肴,激发出无限的愉悦和享受的情感。
当然人类这三个智能层次深度关联,相辅相成。灵性智慧思维是人类智能的最高层次。
与人的智能分类相应,人工智能通常可以分为三个级别,即弱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 (也称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
弱人工智能是指能在某个特定条件下应用的人工智能,如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等。弱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人类某些具体定义下的逻辑推理。尽管它有时可以达到或超过人的能力(如下棋),但其实它并不真正拥有智能。一旦规则改变,它不会自主演进,即没有意识,不具备主观能动性。
通用人工智能是指具有和人几乎同等的智能,包括具有自觉意识、自主演进以及主观能动性。
而超人工智能则是指将来的一种可能,智能机器或许可以具备超越人类智慧的智能。
在后两个阶段,人工智能既可以成为人类的朋友,也可能成为人类的敌人。所以,许多人工智能专家以及科技推动者早已联名呼吁人们必须警惕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的可能灾难,并建立了以安全利用人工智能为宗旨的联盟——未来生命学院(Future Life Institute) 。
今天,无论媒体对人工智能描绘的多么神奇,无论IBM的深蓝(DeepBlue)以及谷歌阿法狗(AlphaGo)在和人类对弈过程中如何凯歌高奏,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弱人工智能这个初级阶段。
也就是说,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仅仅能够实现人类在非常有限条件下的逻辑推理,只能在人类事先设定的算法规律下进行学习。它对人的智慧思维比如意识、知觉和情感还无能为力,还不具备主观能动性。
不具备主观能动性的弱人工智能在不涉及生命安全的领域中可以大有作为,如智能家具、智能娱乐、智能制造、智能服务等。对自动驾驶而言,弱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够为辅助自动驾驶级别提供广泛的应用空间,使它真正成为人们安全愉悦驾驶的好帮手。
但是,对于无人驾驶来说,弱人工智能技术能提供的应用空间还很有限,尚不能支持无人驾驶所必要的主观能动性的实现。
数字技术的局限
尽管无法证明,但我猜想从弱人工智能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主要障碍来自数字计算技术。对通用人工智能来说,数字计算技术可能是一种相对落后的技术。
数字计算本质上是布尔逻辑推理(Boolean Logic) 的产物。布尔逻辑推理中最重要的定律是排中律,即所谓的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基于二进制的数字计算机最基本的计算单元比特只有0和1两种状态,因而在数字计算机中一切信息的表达和运算都是用0和1 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所有信息在数字计算机中都以一种离散的数字形态存在。
然而,自然界中的变量几乎都是连续的,人类的思维乃至生命过程更是连续的。当我们用数字计算处理信息得到简明快速优越性的同时,付出的却是失去信息连续性这一重大代价。